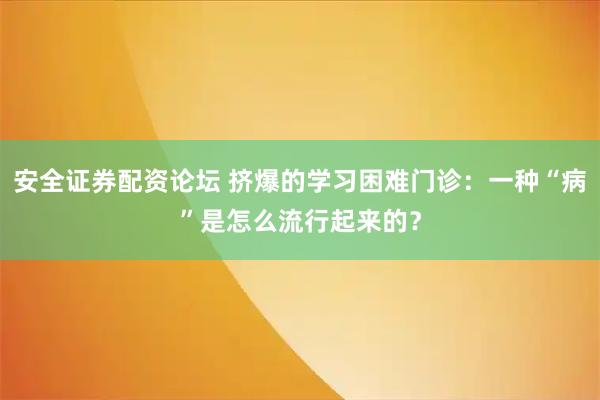
 安全证券配资论坛
安全证券配资论坛

VOL 3546
娄月站在心理科诊区走廊的一侧,手里攥着一沓刚出炉的报告。纸张堆叠着,她有些急切地翻找,目光越过那些她无暇细究的曲线和表格,终于,在其中一张的末尾,她发现了那一行能看明白的诊断结果。
“受试者具备ADHD多动冲动型症状。”
为了这行字,她经历了一场难度不亚于抢演唱会门票的战斗。在预约界面输完验证码,屏幕上跳出的,往往是“该号源已被预订”。
为了这行字,她和女儿付出了1493元的诊费。
而现在,这行字躺在她手里,像一块终于落地的石头,沉重,却也带来一丝诡异的平静。她的女儿,在上海一所双语学校读四年级,从今天起,成了一个“A娃”。
文 | 周游
图 | 中国新闻周刊、Pexels
(原文发布于《中国新闻周刊》,有删改)

浪潮:“以为这里可以提分”
如果学习困难成了一种“病”,你会带孩子去看医生吗?
答案是肯定的,并且队伍已经排得很长。自2021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开设国内最早的学习与阅读障碍门诊起,这类门诊开始在全国各地“冒头”。

2024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学习与阅读障碍门诊出具的患儿近红外脑功能检查报告。
图/受访者提供
首都儿科医学中心2022年开设的学习困难门诊,每月接诊约300人,号源在几秒钟内就被抢光。难度,不亚于一场热门演唱会的门票。
“学习困难门诊的门诊号大概提前一周就会约满。”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主治医师黄懿钖介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陈立则观察到,每到暑假,期末考试暴露出的问题,会进一步放大这种就诊需求。
陈立是今年4月发布的《学习困难门诊规范化建设专家共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她解释,学习困难只是一类症状,其背后的病因极其多样,多与神经发育性障碍相关,如(ADHD)、智力障碍、阅读障碍、运动协调障碍等。同时,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和网络沉迷也很常见。
显然,学习困难门诊不只看一种病。但黄懿钖观察,门诊里确诊最多的还是ADHD,因为它本身就是儿童青少年最高发的精神疾病之一,发病率在5%到15%之间。这些孩子的大脑发育比同龄人“慢半拍”,自我控制能力差,显得更为“幼稚”,因此更容易被发现。
学习困难门诊这个名字,精准地呼应了广大家长的需求。陈立认为,如果医院只设ADHD或阅读障碍门诊,很多家长会因“病耻感”而忌讳,耽误孩子的诊治。而“学习困难”,听起来更像一个便民的、中性的入口。
正视医学问题本是好事,但被焦虑驱使的盲目,也构成了门诊的另一幅景象。多位医生观察到,甚至有家长带着两岁多的孩子来看数学学习困难。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副院长叶敏捷将这些家长形容为“一窝蜂”,尽管门诊能帮助识别病因,但不乏有人只是因为“不甘落后”,甚至“以为这里可以提分”而来。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孩子需要来?叶敏捷建议家长关注“三个不匹配”:第一,能力与成绩不匹配,孩子很聪明,但成绩很差;第二,努力与成绩不匹配,花十分力气,只得到一两分的结果;第三,发展过程不连续,比如孩子四岁了还讲话不清,记不住简单歌词。这些,都可能是需要专业评估的信号。

诊断:在量表与谈话间寻找答案
当刘莹站在诊室外,内心忐忑不安。她既想要一个确切的结果,又害怕那个“期待已久”的结果正式落地。
诊室内,她的儿子正在接受一系列评估:“学障认知加工评估”“学障视知觉评估”“学障书写障碍评估”。其中一项,是让他朗读一篇四年级的课文,看有无错漏,并计算一分钟内能读多少字。
学习困难门诊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精准定位困难的来源。但这个过程,远比想象的复杂。
“我在老家看了好几所医院,医生随便问几个问题,就说是ADHD,要给孩子开药。”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来自河北的母亲冯娟表达着她的疑虑。她的儿子上课总走神,写字很慢。
但在北医六院,医生开具了血液检测和行为评估后告诉她,孩子问题不大,逻辑思维甚至超前,只是专注力一般,并没有病理性的学习障碍。

2025年7月1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诊区,候诊家长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
“目前,全国许多地方的学习困难门诊是名不副实的。”叶敏捷坦言。有些医院为了迎合热度而挂牌,但专业配置不达标,甚至还有线上门诊。“有的医院评估手段也不够,扔给家长几个表格,填完了就诊断是ADHD。这类案例太多了。”
专业的诊断,远非几张量表能够完成。黄懿钖最近接诊的9岁男孩小满,全面发育迟缓,所有科目不及格。最初怀疑是精神发育迟滞,但智力检查只在迟钝边缘。黄懿钖没有止步于此,她进一步开具了脑电图和头颅核磁共振,结果发现,小满的脑部有血管畸形,影响了语言和视觉中枢的功能。
更何况,许多病因并不涉及能被仪器轻易捕捉的器质性病变。长期研究阅读障碍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虹指出,相关的脑部病变常是功能性的,而非结构性的,静态扫描很难发现问题。
因此,医生的专业性至关重要。诊疗,在医生和患者家人的对谈间就已经开始。“很多时候,医生会问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例如‘感觉孩子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叶敏捷说,“但家长回答的内容和神情语气就能透露海量信息,包括父母与孩子的互动模式,孩子是否缺乏安全感等等。”
《专家共识》明确提出,一个合格的学习困难门诊,需要有5年以上相关经验的专科医生、有资质的心理行为测评师、教育干预治疗师等组成的完整团队。它适合开设在能方便转诊的专科儿童医院或大型综合医院的儿童保健科或发育行为儿科下,而不是一两个医生挂个牌子就能做的。

解药:药片、家庭与一间“能接纳变量”的教室
在诊断之后,家长们面临着更艰难的选择:如何干预?
首当其冲的是药物。专注达,药品名盐酸哌甲酯,是治疗ADHD的常用药,却也是让许多家长望而却步的存在。娄月就因为担心副作用,想等孩子青春期后再用药。
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曾亲身体验过专注达,他坦言,药物的确能提高效率,但代价是入睡困难和情绪波动。然而对另一些“A娃家庭”,这种被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又是“救命药”,一旦断药,“天都塌了”。
“最关键的还是对症。”叶敏捷指出,如果孩子不患ADHD,吃“聪明药”也聪明不起来。在一些基层或民营医院,用药不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医生开具缺乏足够循证医学证据的小儿智力糖浆。
“治愈孩子前要先治愈父母。”这是许多一线医生的共识。叶敏捷曾接诊过一个三年级的男孩,父母在场时他一言不发,而当父母离开后,医生一句“你觉得委屈吗”,就让男孩流下泪来。他后来发现,这个家庭“我说你听着”的命令式交流,成了孩子学习能力的封印。

2024年8月,浙江嘉兴市一家公立医院学习困难门诊出具的患儿视听整合连续测试报告。
图/受访者提供
因此,理想的诊疗模式,是一个家、校、医协同的体系。医生提供方案,家长改善养育环境,学校则负责配合专业的康复指导。然而,这其中最欠缺的一环,恰恰是学校。
刘莹曾向学校申请为儿子延长考试时间,被校方拒绝。在现有的考试体制和师生配比下,想让老师关注到每个学习困难的孩子,近乎奢求。
黄懿钖认为,有些实践并不需要挤占太多时间,比如,让ADHD孩子坐在老师眼神能经常覆盖的地方,当他走神时,老师悄悄走到身边,轻抚一下他的肩膀,这种自然的、积极的关注就非常重要。
但大多数老师对此缺乏认知。叶敏捷认为,本质上是目前的中小学教育过于趋同,难以接受“变量”。一个ADHD孩子可能不够专注,但创造力和想 象力却可能很出众,就像达·芬奇。但在“40分钟乖乖听完一堂课”的语境下,这些天赋很难施展。
令人欣慰的是,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老师开始主动联系陈立等专家,希望了解如何为班上的特殊孩子创造更公平的教育环境。
“既然人群中不同性格的人能被接受,那么发育水平的多样性也应被接受。”陈立说。在成长早期,谁也不知道这些孩子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成就。
“对于有阅读障碍的孩子来说,每个字、每一个句子都是难以战胜的可怕‘怪兽’,”李虹教授说,“父母、学校应站在孩子这边,和他们一起打‘怪兽’,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带着病耻感的孤独战士。”
文中刘莹、娄月、小满、冯娟为化名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文章版权归「大米和小米」所有,未经许可,严禁复制、转载、篡改或再发布。本号长期征集线索/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提供线索/投稿请联系:contents@dmhxm.com。
点击拨打大小米服务热线
杨帆证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